很多朋友对于身出礼义之乡和身在他乡是吾乡不太懂,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!
本文目录
一、急求《礼记·冠义》翻译
1、人之所以成其为人,在于有礼义。礼义从哪里做起呢?应从举止得体、态度端庄、言谈恭顺作起。举止得体,态度端庄,言谈恭顺,然后礼义才算完备。以此来使君臣各安其位、父子相亲、长幼和睦。君臣各安其位,父子相亲,长幼和睦,然后礼义才算确立。所以说,只有行过冠礼以后才算服装齐备,服装齐备以后才能做到举止得体、态度端庄、言谈恭顺。所以说,冠礼是礼的开始。所以古时候的圣王很重视冠礼。
2、古人在举行冠礼时,要先通过占签选定吉曰、通过占笠选择一位可以为子弟加冠的宾,以此来表示对加冠之事的重视。对加冠之事的重视也就体现了对礼的重视,对礼的重视体现了礼是治国的根本。在昨阶上为嫡子加冠,这表示嫡子是未来的继承人。在客位对冠者行酪礼,这表示他已受到了 *** 的尊重。三次加冠,一次比一次加的冠尊贵,这是要启发冠者立志向上。
3、行过冠礼以后,对冠者要称字而不称名,这因为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。加冠以后去拜见母亲,母亲答拜;去见兄弟,兄弟对他再拜:这都是因为他已是 *** 而与之施礼。戴上淄布冠,穿上玄端服,拿着礼品去拜见国君,把礼品放在地上,表示不敢直接授受;接着又拿着礼品去拜见乡大夫和乡先生,都是以 *** 的身份前去拜见。
4、既然是 *** 的身份,那就要以 *** 的礼数来要求他。所谓以 *** 的礼数来要求他,也就是将要要求他做一个合格的儿子,做一个合格的弟弟,做一个合格的臣子,做一个合格的后辈。将要要求他具备这四个方面的德行,冠礼能不重要吗!
5、一个人做到,了对父母孝顺,对兄长友爱,对国君忠诚,对长辈顺从,然后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。能被称为真正的人,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。所以圣王很重视礼。所以说,冠礼是 *** 之礼的开始,是嘉礼当中重要的一项。所以古人很重视冠礼。因为重视冠礼,所以冠礼要在宗庙之丙进行。在宗庙之内进行,是表示郑重其事。由于郑重其事,所以不敢擅自处理此事。因为不敢擅自处理此事,所以要在宗庙之内进行,表示自卑,表示对先祖的尊重。
6、凡人之所以为人者,礼义也。礼义之始,在于正容体、齐颜色、顺辞令。容体正,颜色齐,辞令顺,而后礼义备。以正君臣、亲父子、和长幼。君臣正,父子亲,长幼和,而后礼义立。故冠而后服备,服备而后容体正、颜色齐、辞令顺。故曰:冠者,礼之始也。是故古者圣王重冠。
7、古者冠礼筮日筮宾,所以敬冠事,敬冠事所以重礼;重礼所以为国本也。故冠于阼,以着代也;醮于客位,三加弥尊,加有成也;已冠而字之, *** 之道也。见于母,母拜之;见于兄弟,兄弟拜之; *** 而与为礼也。玄冠、玄端奠挚于君,遂以挚见于乡大夫、乡先生;以 *** 见也。
8、 *** 之者,将责 *** 礼焉也。责 *** 礼焉者,将责为人子、为人弟、为人臣、为人少者之礼行焉。将责四者之行于人,其礼可不重与?故孝弟忠顺之行立,而后可以为人;可以为人,而后可以治 *** 。故圣王重礼。故曰:冠者,礼之始也,嘉事之重者也。是故古者重冠;重冠故行之于庙;行之于庙者,所以尊重事;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;不敢擅重事,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。
9、出自《礼记·冠义》,选自西汉戴圣所编的《礼记》。
10、《礼记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 *** 选集,共二十卷四十九篇,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,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(如天道观、宇宙观、人生观)、教育思想(如个人修身、教育 *** 、教学 *** 、学校管理)、 *** 思想(如以教化政、大同社会、礼制与刑律)、美学思想(如物动心感说、礼乐中和说),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,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。
11、自东汉郑玄作“注”后,《礼记》地位日升,至唐代时尊为“经”,宋代以后,位居“三礼”之首。《礼记》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,对儒家文化传承、当代文化教育和德 *** 教养,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。
12、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、辞令、服饰、家教、尊老、丧祭、教化、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,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,对于读古书,传承中华文明,是难得的文化宝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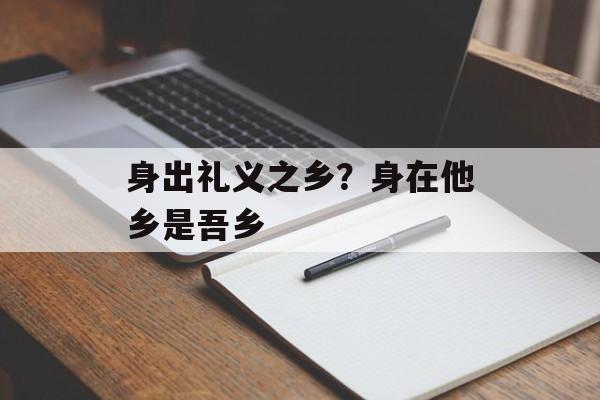
13、《礼记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,《礼记》在曹魏时期升格为“经”,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“五经”之一,取代了《仪礼》的地位;《礼记》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,被尊为“四书”之一。
14、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-礼记·冠义
二、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下一句
1、“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”下一句是:【万钟于我何加焉】!
2、“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”出自《孟子鱼我所欲也》,全文如下:
鱼,我所欲也;熊掌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,亦我所欲也;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;死亦我所恶,所恶有甚于死者,故患有所不避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,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?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,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?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,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。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,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,人皆有之,贤者能勿丧耳。
一箪食,一豆羹,得之则生,弗得则死。呼尔而与之,行道之人弗受;蹴尔而与之,乞人不屑也。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,万钟于我何加焉!为宫室之美,妻妾之奉,所识穷乏者得我与?乡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宫室之美为之;乡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妻妾之奉为之;乡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;是亦不可以已乎?此之谓失其本心。
鱼是我所想要的,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,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,我宁愿舍弃鱼而选取熊掌。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,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,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,我宁愿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。生命是我所喜爱的,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,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;死亡是我所厌恶的,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,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。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,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,有什么不可以使用呢?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,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 *** 哪会不采用呢?采用这种做法就能够活命,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;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,可是有的 *** 不肯采用。是因为有比生命更想要的,有比死亡更厌恶的。并非只是贤人有这种本 *** ,人人都有,只是贤人能够不丧失罢了。
一碗饭,一碗汤,得到它就能活下去,不得到它就会饿死。可是轻蔑地呼喝着给人吃,饥饿的行 *** 不愿接受;用脚踢给别人吃,乞丐也因轻视而不肯接受。 *** 厚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它。这样, *** 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?是为了住宅的华丽,妻妾的侍奉和认识的 *** 感激我吗?以前(有人)宁肯死也不愿接受,现在(有人)却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它;以前(有人)宁肯死也不愿接受,现在(有人)却为了妻妾的侍奉却接受了它;以前(有人)宁肯死也不愿接受,现在(有人)为了认识的 *** 感激自己却接受了它。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?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本 *** 。
4、《鱼我所欲也》选自《孟子·告子上》,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:义重于生,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。
三、是“礼仪之邦”还是“礼义之邦”(2)
历久弥新:礼之“仪”“义”的纠结
除了“礼义之邦”“礼仪之邦”,文献中也经常出现“礼义之乡”“礼义之国”“礼义之朝”“礼仪之国”等概念。
据初步翻检,“礼义之乡”可能最早见于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(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2118页),“礼义之国”可能最早见于《汉书》(《高帝纪》《赵充国辛庆忌传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50、2987页),而“礼义之朝”可能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(514年)(宋郑居中等《政和五礼新仪》之《政和御制冠礼》卷5),“礼仪之国”则可能最早见于清人黄遵宪所撰《日本国志·邻交志上一》。“礼义之乡”自出现一直沿用到1937年,而“礼义之国”沿用到清季,指称与“礼义之邦”基本一致;其前也有冠以“忠信”“忠节”“文学”(“礼义之乡”),或“守节”“诗书”“衣冠”“冠带”“文章”(“礼义之国”)等词者;相较而言,“礼义之朝”(除梁武帝外,宋人吕元泰、元人郝经也曾使用)、“礼仪之国”则较为少见。
传统中国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的需要,礼越来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其间,既有文献解说的积淀充盈,也有典章 *** 的应时 *** ,更有身体力行的规范引导。在此文化氛围之下,三礼(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)、四礼(冠、婚、丧、祭)、五礼(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)纷然而起,礼仪、礼制、礼俗竞相杂陈,守礼、行礼、变礼与时变化,等等。究其归趣,清代大儒顾炎武所谓“礼者,本于人心之节文,以为自治治人之具”,可谓一语破的。然而,自先秦以来,关于礼之义与仪的判别,则一直或显或隐地纠结着人们的思维。
如公元前537年,鲁昭公“如晋,自郊劳至于赠贿,无失礼”。对此,晋侯以为他“善于礼”。然而,女叔齐却有不同的看法,认为鲁昭公不知礼。晋侯问其故,女叔齐回答:“是仪也,不可谓礼。”那么,什么是礼呢?他解释说:“礼,所以守其国,行其政令,无失其民者也。”而反观鲁国现状,则与礼之要求相去甚远。所以女叔齐不无遗憾地感慨道:“礼之本末,将于此乎在,而屑屑焉习仪以亟。言善于礼,不亦远乎!”又如公元前517年,赵简子向子大叔问“揖让 *** 之礼”。子大叔回答:“是仪也,非礼也。”赵简子追问:“何谓礼?”子大叔对道:“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:夫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,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,因地之 *** ,生其六气,用其五行。气为五味,发为五色,章为五声, *** 则昏乱,民失其 *** 。是故为礼以奉之。”赵简子感叹说:“甚哉!礼之大也。”子大叔又回应道:“礼,上下之纪,天地之经纬也,民之所以生也,是以先王尚之。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,谓之 *** 。大,不亦宜乎!”《礼记》中也强调:“礼之所尊,尊其义也。失其义,陈其数,祝史之事也。故其数可陈也,其义难知也。知其义而敬守之,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。天地合,而后万物兴焉。”
对于礼教大为痛恨的吴虞,通过梳理前人有关的礼论,也曾感慨:“夫谈法律者,不贵识其条文,而贵明其所以 *** 之意;言礼制者,不在辨其仪节,而在知其所以制礼之心。”柳诒徵先生则强调:“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,坐以仪为礼也。仅知仪之为礼,故限于史志之记载典章 *** ,而若纪表列传之类不必根于礼经。不知典章 *** 节文等威繁变之原,皆本于天然之秩叙。”诸如此类的言论,无不表明对礼义重要 *** 的重视。
当然,由于古今情势的不同,仅仅强调礼义,也不免产生偏差。对此,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曾分辩道:“古者礼乐之书具在,人皆识其器数,却怕他不晓其义,故教之曰:‘凡音之起,由人心生也。’又曰:‘失其义,陈其数者,祝、史之徒也。’今则礼、乐之书皆亡,学者却但言其义,至以器数则不复晓,盖失其本矣。”这一认识,可谓通达之论。
由此观之,礼义之乡、礼义之国、礼义之邦、礼义之朝、礼仪之邦、礼仪之国等词的使用,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,皆为“历史的存在”,其间的兴替,是与时代、时势、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的,并非仅为误用、滥用的问题。“礼义”与“礼仪”亦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物,其关键乃在于如何因时因势把握其间的度。诚如宋儒程颐所强调的:“礼者,理也,文也。理者,实也,本也。文者,华也,末也。理文若二,而一道也。文过则奢,实过则俭。奢自文至,俭自实生,形影之类也。”总之,“礼乎礼!夫礼所以制中也”。而礼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?它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?礼的内涵和实质又是什么?怎样才能把握礼的内在意义与外在表现的度?凡此种种,皆是历久而弥新的话题,需予以认真地反思和探究。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关于身出礼义之乡,身在他乡是吾乡的介绍到此结束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